遇见肿瘤大咖魏丽惠不仅是女人,更是
2017-3-12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卷首语遇见·肿瘤大咖
默沙东中国官方 疾病面前,女性常常是脆弱的。
40年前,在肿瘤还不高发的年代里,卵巢癌成为了妇科医生和女人的噩梦。无论医生如何全力以赴,最终都是手术化疗医院,不久又排着队送往太平间。人们对卵巢癌如此恐惧,以致于曾提出对45岁以后的女性,为了避免卵巢癌,全部切除双侧卵巢和输卵管——对女人来说,预防肿瘤代价何其大。
当时,有一对双胞胎的母亲,罹患卵巢癌,在那个彩电刚刚普及的年代里,她的孩子连黑白电视都没有看过。年幼的孩子对爸爸说:“我们本来可以有电视机,可是因为妈妈病了,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一年多后,他们连妈妈也没有了。
从此,魏丽惠决定研究妇科肿瘤,成为了国内最早研究卵巢癌的医生之一。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拯救一个女人,就是拯救一个家庭。
当女人成为母亲,就会变得异常坚强。
为了孩子,一个女人柔弱的身体竟能承受7次手术和53次化疗,终于把女儿从5年级一直陪伴到大学毕业才放手。这个患者让魏丽惠教授至今难忘。
她是一位外交学院的副教授,刚从国外学习回来就查出卵巢癌,当时判断的存活期只有半年。然而在本人强烈的求生欲望、家属的全力配合和医生的努力下,她整整存活了11年。
“给了她女儿一个完整的家庭,这就是妇科肿瘤医生最大的成就感。”魏丽惠教授说。这种成就感,别人难以体会到。
患者临终前,一定要见魏丽惠教授最后一面。这样的送别,魏丽惠教授一生经历很多次。在那个年代,医患之间是如此真诚,她们只想见到自己的医生,表达最后的谢意。
这样的送别,医生纵然深感无力,也不能表示难过,魏丽惠说:“要让病人走得安详,我会和她们说,一切都挺好的,你也挺好的,你好好睡觉。”
陪宫颈癌“准妈妈”一起走钢丝如今最让魏教授牵肠挂肚的是两名年轻的患者。全科的医生和她们在一起冒险,探索一条在中国无人走过的路——妊娠合并子宫颈癌,一边保胎一边化疗控制病情,直至剖宫产把孩子生下来。
这两位年轻的妈妈,一个26岁,是第二胎;一个24岁,是第一胎,都是怀孕20周时查出宫颈癌。按照常规,她们应该终止妊娠做根治性手术,然而对24岁的张悦(化名)来说,这将意味着她永远无法再生育自己的孩子,她求医生让自己把孩子留下来。
魏丽惠教授和她的团队充分查找了各种科学依据,查找国外文献,得到信心后,全科室的医生们决定陪她们一起走钢丝。在至今10个月的治疗中,张悦经历了孕期3次化疗、产后8次放化疗和介入治疗,共11次的治疗,她都咬牙挺了过来,肿瘤已经明显缩小。
医生团队们更是小心翼翼。魏教授把自己的私人 这种踩着钢丝的成就感,别人也难以体会。
如果她们冒险成功,魏丽惠教授和她的医生们就为这样的中国女性患者找到了一条希望之路。要知道,当年,明星李媛媛在孕期查出患宫颈癌二期后,选择了生完孩子才治疗,产后仅存活了一年半。
医学,正是在患者和医生相互信任的携手探索中得以进步。
魏丽惠教授说:“我很感动,她们为孩子这么努力。”
成为患者,是她人生最难的课题
当医生成为患者,却是她人生最难的课题。
8年前,魏丽惠教授被发现肺上长了东西,尽管病灶很小,作为手术医生,她果断决定马上切掉。
手术前一天,她去科里转了一圈,看了学生和同事,并交待“你们别来看我,手术后就告诉我手术是大还是小就行。”然后装作毫不在意,故作轻松地回病房了,“其实我心里很在意。”魏教授笑着回忆。
晚上,她问自己的管床医生,手术准备怎么做?对方说:“切完我就给你送个冰冻,要是癌,咱们就扩大,包括淋巴。”双方都装作轻描淡写,就像随意在聊一个小手术。
其实,彼此都十分在意。“他们不敢跟我说太深太多,又根本瞒不住我。”魏教授说,“尤其当我听到淋巴还要切,心里一惊,‘说明你们估计得不那么早期啊’。”但她什么也没说,怕影响医生。
这是只有医生之间才能懂的微妙和善意。
第二天她在ICU醒来,根本不用问手术大小,只问一句“现在几点了”,通过手术用时她就明白了——手术做得不小,这就是医生患者与普通患者不同之处。
魏教授坦言,手术前,她连自己的片子都不敢看,直到做完手术四五年之后,她一看片子才明白,难怪手术做的这么大,“病灶尽管很小,但中间有一根血管像针一样插了进去,就说明这个病灶很快要活跃了。”她说。四五年之后,同事们才告诉她实情:当时实际分析70-80%可能是肿瘤,20-30%是炎症,但手术前告诉她是各占50%。
“我还是肿瘤医生啊,生病时,我都会想这么多,我怕家人有负担,又怕真的严重,怕很多东西。”魏丽惠教授说。
她说,当医生成为了患者,真正体会到病人的迷茫、焦虑、为难和猜测。“这是对生命的猜测,不是畏惧死亡,只是不知道生命能允许我们活多久,又会对家人带来什么样的损失。”
“什么我都经历过了,战乱、“文革”、上山下乡,非典、地震,连肿瘤我都得过了。健康和家人,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魏丽惠教授说完,一脸平和的微笑。
作为外婆,她将如何给外孙女打HPV疫苗?
这几天,关于HPV病毒、宫颈癌、疫苗的科普文章如泄洪之水,秒淹手机屏。我坐在魏教授面前时,问了她两个问题:您会让您9岁的外孙女打这个疫苗吗?如果打,何时打?
与媒体把疫苗炒得热火朝天相比,处于热点中心的魏丽惠教授却很平静。年过七旬的她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7年,对于医生、科研人员来说,这个过程漫长、艰苦而沉寂。
此次做疫苗的临床试验,魏丽惠教授感触最深的就是,这一次中国是完全按照国外的标准走了一条很严谨的道路,从执行手册,到每次的筛查、随访,操作过程都一板一眼做得非常严谨,对中国医生和疾控中心研究员都是一次非常好的训练。
“疫苗是一个很慎重的事,需要很小心。”她说。
所以几年来,中国的专家们天天呼吁上市,可是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们顿感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毕竟疫苗作为疾病的一级预防措施,面对的是大规模的健康人群,一旦从研究阶段到批准上市,大规模推广使用时,安全性就是这些专家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总结的是整体和全局,但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的,还是“能不能打,何时打”这样的实际问题。这个问题,同样也摆在魏丽惠教授面前,因为她是一名9岁小女孩的外婆。
魏教授说:“给外孙女打疫苗对她是很有益处的,但什么时候打,现在9岁,我认为有点早,希望等她再长大一些,十几岁再打对她会更好。”
作为医生和科学家,她观察和跟踪了成千上万人注射疫苗后的反应,她知道这个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符合科学标准的。但作为一个小女孩的外婆,她依然会很慎重地为外孙女做决策,因为对于个体来说,每一次注射后的反应都是未知。所以“疫苗是一个很慎重的事,从国家出台政策,到个人做决定,都需要谨慎。”她再次强调。
遇见大咖系列回顾第1期沈琳:对于患者生命,医院比谁都“贪婪”
第2期吴一龙:世界肺癌的“中国贡献”
第3期徐兵河:把照顾晚期乳腺癌患者当“特权”
作者简介:戴戴(戴志悦)
独立医疗媒体人,著有北京看白癜风医院地址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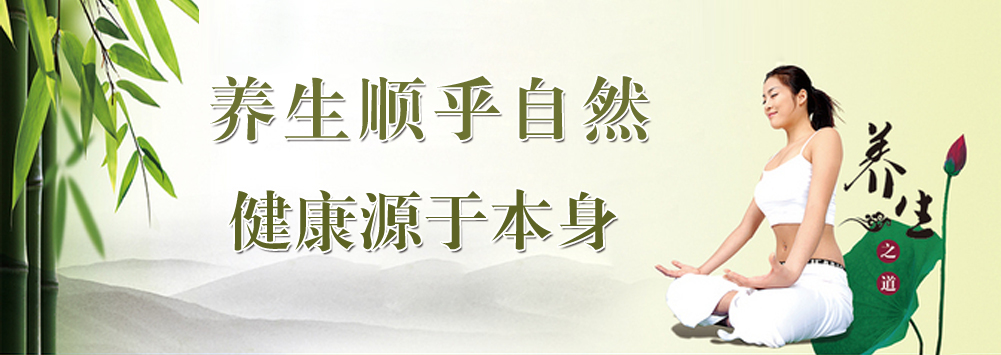
 健康热线:
健康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