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卵巢上皮性癌化疗耐药的研
2021-2-2 来源:本站原创 浏览次数:次白癜风初期能治好么 http://m.39.net/pf/a_5683025.html
选自:中华妇产科杂志年5月第55卷第5期
作者:冯利园李力
广西医院妇瘤科暨区域性高发肿瘤早期防治研究教育部重点室验室,南宁
通信作者
李力,Email:lili
gxmu.edu.cn摘要化疗耐药是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治疗中尚未解决的主要障碍,卵巢癌化疗耐药患者迫切需要探索新的药物或治疗策略。DNA甲基化是最早发现并且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学修饰,越来越多的临床试验显示,去甲基化药物可以恢复卵巢癌化疗耐药患者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改善预后。本文就预测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甲基化标志物、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药物调控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可能机制、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卵巢癌化疗耐药的临床研究等进行综述。
卵巢上皮性癌(卵巢癌)是女性生殖系统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其死亡率居首位,由于卵巢癌的临床症状不明显,发病隐匿,缺乏可靠的早期检测方法,约75%的卵巢癌患者初次诊断时已为晚期,5年生存率低于30%[1?2]。针对初次诊断的卵巢癌患者,其标准治疗方案是最大限度地行肿瘤细胞减灭术,术后辅以铂类药物为基础的联合化疗[3]。近年来,随着根治性手术的进步和化疗方案的发展,使得卵巢癌的疗效较前有所改善,但卵巢癌细胞的原发性或继发性化疗耐药,往往导致化疗失败,是引起卵巢癌复发、转移及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关键环节,严重制约了卵巢癌患者生存率的提高[4?5]。为了改善卵巢癌患者的预后,需要新的能够早期预测化疗耐药的标志物以及克服耐药性的新的治疗策略。
导致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复杂多样,除了遗传因素外,还涉及大量的表观遗传学改变[6?7]。DNA甲基化是最早发现并且研究最多的表观遗传学修饰,是指在DNA甲基转移酶(DNMT)的作用下,以S?腺苷?L?甲硫氨酸为甲基供体,将甲基转移到胞嘧啶的5位碳原子上,生成5?甲基胞嘧啶的过程。研究显示,异常的DNA甲基化与卵巢癌铂类药物获得性耐药有关,去甲基化药物可恢复卵巢癌化疗耐药患者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改善其预后,是潜在的卵巢癌治疗的靶点[8?9]。本文就预测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甲基化标志物、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药物调控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可能机制、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卵巢癌化疗耐药的临床研究综述如下。
一、预测卵巢癌化疗敏感性的甲基化标志物目前,临床上还没有可靠的方法来预测卵巢癌铂类药物耐药。DNA甲基化作为生物标志物具有化学稳定性、可以定量分析、耐药相关的甲基化变化通常发生在耐药开始之前、非侵袭性检测(可以在患者的体液中检测到)等优势。随着DNA甲基化检测平台和技术的更新,越来越多参与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基因被报道。除了早期研究发现的BRCA1、DNA损伤修复通路相关基因(包括GSTP1、FANCF和MGMT)、PTEN、RASSF1、MDR1基因的高甲基化与化疗敏感性呈正相关外,近几年新增的与卵巢癌化疗耐药相关的DNA甲基化研究至少有H3K79[10]、TET1、MLH1、SERPINE1[11]、TRIB2[12]、KLF4、FZD10、ZNF[13]、ABCB1[14]、hMSH2[15]等基因。Tomar等[16]分析两组极端化疗结局(即铂类药物化疗完全反应者8例和完全不反应者10例)的卵巢癌患者的DNA甲基化,并在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中进行验证,结果发现,两种化疗结局患者之间有45个存在显著差异的DNA甲基化和表达基因;在相同的测序样品中,焦磷酸测序证实了9个差异显著的甲基化基因,包括FZD10、FAM83A、MYO18B、MKX、GLI3、TMIG2、TMEM40、NEUROG3和HOMER3基因;外部验证队列中,最终有4个候选基因(FZD10、FAM83A、MYO18B和MKX)在两种化疗结局患者之间至少有1个存在显著差异的二核苷酸胞嘧啶(CpG)位点,在这4个候选基因中,FZD10和MKX基因的高甲基化提示化疗有效,而FAM83A和MYO18B基因的高甲基化提示化疗无效。超过50%的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在二线化疗中对铂类药物的化疗无反应,二线化疗方案的选择,主要根据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决定,对于PFS≤6个月的患者,二线化疗方案建议选择其他新的治疗方案[17]。Flanagan等[18]将卵巢癌患者化疗前与化疗后复发时的血液DNA匹配样本进行比较,发现铂类药物本身可以诱导卵巢癌患者特异性甲基化位点的异常甲基化;在调整了年龄、手术病理分期、残留灶大小、病理类型后,cg、cg、cg、cg、cg、cg、cg、cg这8个位点的高甲基化与铂类药物化疗后患者的PFS仍然显著相关,可以帮助指导患者选择二线治疗方案。尽管DNA甲基化作为标志物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但其预测卵巢癌铂类药物化疗敏感性仍然是1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未来需要应用更多的全基因组检测方法,筛选出具有高特异度和敏感度的鉴定铂类药物化疗耐药的DNA甲基化位点。
二、DNA甲基化和去甲基化药物调控卵巢癌化疗耐药的可能机制进一步了解导致化疗耐药的分子机制对治疗新策略的发现是必不可少的[19]。化疗药物通过引起DNA损伤、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等多种途径杀死肿瘤细胞,这些相关通路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水平异常可沉默基因表达从而导致化疗耐药。其中,已有研究报道的通过细胞凋亡参与化疗耐药调控的异常甲基化基因有MLH1、PTEN、FBXO32、RASSF1、TNFRSF10A、BLU、RGS10、UCHL1、MDR1、Sulf?1、HOXA9、FZD10、MSX1[20]等;通过细胞增殖参与化疗耐药调控的异常甲基化基因有TGFBI、UCHL1、SFRP、HOXA10、TMEM88[21];通过参与蛋白激酶B(Akt)信号通路调节细胞凋亡和增殖,参与化疗耐药调控的异常甲基化基因有PTEN、BLU、HIN?1[22?23]。除细胞凋亡、细胞增殖、Akt信号通路外,DNA甲基化基因还可以通过其他机制参与卵巢癌的化疗耐药。年,Cacan[24]的研究显示,耐药卵巢癌细胞中DNA甲基化降低了T淋巴细胞激活配体4?1BBL(即CD)和OX?40L(即CD)的表达,这种免疫抑制机制有助于癌细胞逃避化疗刺激的免疫反应从而造成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下降。在难治性卵巢癌患者中,顺铂可诱导基因间区的低甲基化。最近的研究表明,发育调控基因MSX1和TMEM88的低甲基化与卵巢癌铂类药物耐药之间存在相关性[25]。甲基化水平的改变可调节上皮细胞向间质的转化,这也是铂类药物耐药的重要调控机制。研究发现,甲基化调控非编码RNA——HOX基因座转录而来的反义RNA(HOTAIR)和TET、MSX1基因的表达,诱导上皮细胞向间质转化,导致卵巢癌化疗耐药的产生[26?27]。由此可见,DNA甲基化在卵巢癌化疗耐药发生、发展中的调控机制复杂多样,多种甲基化基因之间常相互联系并相互影响,共同导致了卵巢癌的化疗耐药。
相对于基因突变来说,DNA甲基化是可以逆转的,去甲基化药物有可能成为新一代肿瘤治疗的靶向药物。Fang等[28]阐明了去甲基化药物恢复卵巢癌铂类药物化疗敏感性相关的表观遗传学特征,这可能为预测联合使用DNMT抑制剂患者的预后提供了实用价值。该研究比较了接受卡铂加DNMT抑制剂——瓜德希他滨(guadecitabine)或标准化疗方案的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卵巢癌患者的疗效,收集同一批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配对肿瘤活检组织进行表观基因组和转录组分析,发现瓜德希他滨治疗后有94个显著低甲基化的基因启动子,个差异表达的基因,差异表达基因主要参与免疫激活和DNA修复通路。可见,瓜德希他滨抑制DNA甲基化,可能是通过改变与DNA修复和免疫激活相关的基因表达,恢复卵巢癌细胞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Wang和Qiu[29]基于蛋白互作网络(PPI)、致病基因网络预测卵巢癌去甲基化药物地西他滨(decitabine)治疗前、后的关键基因,揭示其分子机制。该研究对致病基因网络中的每个基因分配1个权重,然后对候选基因进行评估,获得了参与地西他滨治疗的5个关键基因PIK3R2、CCNB1、IL?2、IL?1B和CDC6,其中,PIK3R2参与Akt信号通路,在卵巢癌的发生中发挥重要作用;CCNB1调节有丝分裂,其转录导致整个细胞周期中异常高水平的CCNB1,调控细胞增殖;IL?2是抗原活化后产生的1种多效性细胞因子,调节T淋巴细胞的增殖;CDC6是DNA复制的重要调控因子,在细胞周期中对检查点机制的激活和维持起着重要作用,CDC6功能异常会导致DNA损伤和基因组不稳定性。Wang和Qiu[29]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抑制DNA甲基化,是通过改变与DNA修复和免疫激活相关的基因表达,恢复卵巢癌细胞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停用去甲基化药物后部分卵巢癌患者恢复甲基化,表明,去甲基化药物的治疗作用是通过重新调控甲基化介导的,而不是直接的细胞毒性。去甲基化药物的非特异性活性对基因组产生广泛的影响,其引起的化疗再敏效应很可能不是由单个转录本的再表达引起的,而是由基因组广泛重编程以及恶性肿瘤相关通路的激活(或抑制)引起的。总的来说,DNA甲基化通过调控DNA修复、细胞增殖和凋亡、Akt信号通路、免疫激活相关基因的表达等多种机制参与卵巢癌化疗耐药,去甲基化药物改变这些相关通路基因启动子的甲基化水平,调控基因表达,恢复卵巢癌细胞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
三、去甲基化药物治疗卵巢癌化疗耐药的临床研究用于卵巢癌化疗耐药临床研究的DNMT抑制剂主要是地西他滨和瓜德希他滨。年,Fang等[30]进行了低剂量地西他滨联合卡铂治疗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的卵巢癌患者的Ⅰ期临床试验,使用传统的3+3剂量递增研究,对地西他滨进行了2个剂量水平的测试,即10mg/m2和20mg/m2,结果显示,20mg/m2的剂量限制毒性(DLT)为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10mg/m2未观察到DLT;10例患者中,1例患者疗效为部分缓解,3例患者病情稳定大于6个月。提示,地西他滨具有临床疗效,支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随后,Matei等[31]和Fu等[32]的Ⅰ期单臂临床试验均发现,低剂量地西他滨恢复了耐药卵巢癌患者对铂类化疗药物的敏感性,且耐受性良好,未观察到大于4级的不良事件。年,Benson等[33]的Ⅱ期临床试验采用卡铂联合地西他滨治疗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给予患者静脉滴注低剂量(10mg/m2)地西他滨,连续5d,第8天使用卡铂[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5],结果显示,14例患者中,6例对治疗有效,其中1例患者无进展生存时间达17个月。
年,Zhang等[34]纳入了55例复发性卵巢癌患者,比较低剂量地西他滨+紫杉醇卡铂减量化疗或低剂量地西他滨+紫杉醇卡铂减量化疗+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联合治疗在卵巢癌中的临床疗效,根据实体瘤治疗疗效评价标准(RECIST),在地西他滨+紫杉醇卡铂减量化疗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DCR)和客观反应率(ORR)分别为70.00%和22.50%,相比于铂类药物敏感患者,铂类药物耐药患者的DCR更高(分别为61.90%、78.95%);在地西他滨+紫杉醇卡铂减量化疗+杀伤细胞治疗组,患者的DCR和ORR分别达.00%和58.30%,相比于铂类药物敏感患者,铂类药物耐药患者的ORR更高(分别为87.50%、0);并且与铂类药物敏感患者相比,铂类药物耐药患者的PFS(分别为8、2个月)和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9、8个月)均更长;两个治疗方案组最常见的毒性反应均为恶心、厌食、疲劳,大多为1~2级不良反应,未观察到大于4级的不良事件。可见,低剂量地西他滨+紫杉醇卡铂减量化疗方案具有临床获益,尤其是对铂类药物耐药的卵巢癌患者,联合过继免疫治疗对铂类药物耐药的卵巢癌患者可能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瓜德希他滨是第2代DNA去甲基化药物,相比于地西他滨,其在水相中的稳定性提高并且半衰期延长,可有效增加药物在细胞中的运送。Fang等[28]采用卡铂联合瓜德希他滨或标准化疗方案治疗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患者。治疗后6个月,卡铂联合瓜德希他滨治疗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率为37%,标准化疗方案组为13%,说明,瓜德希他滨治疗可诱导铂类药物耐药的卵巢癌患者再敏,具有临床意义。年,曾报道了地西他滨作用的Matei等[35]研究团队又报道了瓜德希他滨和卡铂联合治疗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的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原发性腹膜癌或输卵管癌患者的临床疗效,20例患者予以瓜德希他滨45mg/m2静脉滴注,连续5d,第8天静脉注射卡铂(AUC=5),结果显示,4例患者出现DLT(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导致瓜地西他滨和卡铂剂量分别下降至30mg/m2和AUC=4;3例患者有部分缓解,6例患者疾病稳定3个月,总体缓解率和临床受益率分别为15%和45%;10%的患者出现3级不良事件(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恶心、低钾血症等)。年,Oza等[36]最新发表的Ⅱ期临床试验显示,比较瓜德希他滨+卡铂、二线化疗方案治疗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患者的临床疗效,例患者中,瓜德希他滨+卡铂组51例,二线化疗方案组49例,结果显示,两组间的中位PFS比较无显著差异(分别为16.3、9.1周,P=0.);但随访6个月时,瓜德希他滨+卡铂组患者的无复发率明显高于二线化疗方案组(分别为37%、11%,P=0.);瓜德希他滨+卡铂组和二线化疗方案组的3级以上不良反应发生率相似(分别为51%和49%)。虽然该研究未显示出瓜德希他滨+卡铂组患者的PFS优于二线化疗方案组,但再治疗6个月时,瓜德希他滨+卡铂组患者的无复发率更高。提示,DNMT抑制剂和卡铂联合应用于卵巢癌患者是可耐受的,并表现出生物学活性,在更大样本量的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患者中探索更好的基于DNMT抑制剂的方案是值得的。
四、结论与展望对于复发性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患者,迫切需要探索新的能够早期预测化疗耐药的生物标志物以及新的逆转化疗耐药的药物或治疗策略。鉴于DNA甲基化具有化学稳定性、可以在耐药开始之前检测到的优势,DNA甲基化可以作为预测化疗耐药的标志物用以指导卵巢癌患者的个体化治疗,避免使用无效的治疗手段。DNA甲基化通过调控DNA修复、细胞的增殖和凋亡、Akt信号通路、免疫激活相关基因的表达等多种机制参与卵巢癌的化疗耐药,去甲基化药物可改变这些相关通路基因的启动子甲基化水平,调控基因表达,以恢复卵巢癌对铂类药物的敏感性。对于铂类药物耐药性卵巢癌患者,低剂量的去甲基化药物与铂类药物联合应用是可耐受的,并表现出逆转化疗耐药的临床效果。未来需进一步识别DNMT抑制剂的生物标志物,以找到可能起效的特定人群进行精准给药。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略
本文编辑:姚红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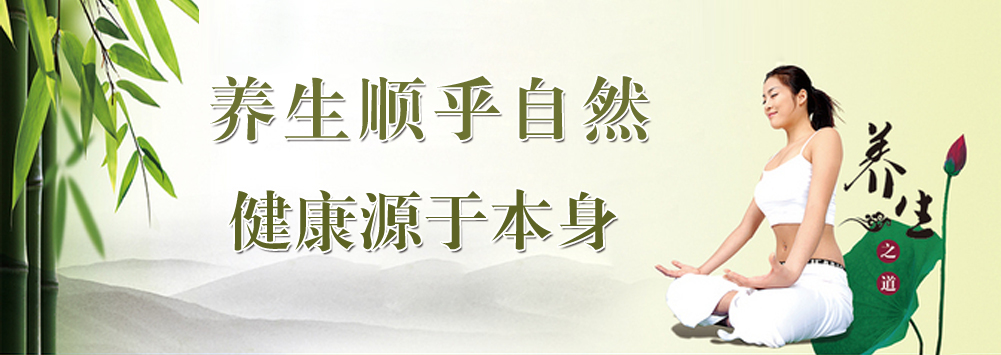
 健康热线:
健康热线: